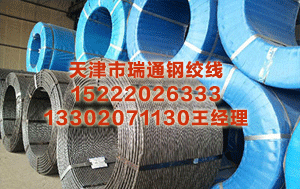1982年夏天,距离福克兰群岛战争停火还不到两个月,伦敦的天空刚刚散去战火的阴霾,唐宁街10号却又被一件事笼罩住了:香港的去留。对英国保守党政府来说,这次并非一场普通的外交谈判,而是一场关于“大英帝国脸面”的较量。
有意思的是,就在英国国内舆论还沉浸在“海军又一次拯救了国”的情绪中时,远在北京,中南海的判断已经非常冷静:香港问题,不能拖,也拖不久。战舰可以绕地球一圈,条约却不可能永远压在一个已经站起来的国头上。
这一南一北的两种心态,决定了之后两年多的中英角力,也让“铁娘子”和“钢铁公司”的对话,写进了一段颇为复杂的历史。
一、英国为何非要咬住香港不放
如果只从地图上看,香港这块地方不算大,但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的英国决策层眼里,它的分量重。撒切尔夫人本人的态度,其实就是那一代英国政治精英真实心态的缩影。
AI辅助天地孪生太空小鼠无人智能实验舱示意图
泰山脊蕊夜蛾翅展约38.0毫米,前翅灰褐,微带淡红或黄褐,翅面上可见数条黑波浪细线,翅中间有两枚相通的灰褐圆斑,另外还有一个较清晰的肾形斑纹;后翅灰褐,翅脉较;腹部3至7节背中央基部具耸起的鳞片簇,以3.4节为明显,这也是脊蕊夜蛾属的显著特征之一。
经济利益是英国人现实的考量。上世纪七十年代到八十年代初,英国国内经济情况并不理想,传统工业衰落,失业率居不下,财政压力沉重。而香港在这一时期已经成为重要的金融和贸易中心,英资机构遍布其中,一年给英国带来的回报,以当时的估算,至少在数十亿港元以上。
不少英国政客在内部会议上讲得很直白:在南非等地的资产可以慢慢调整,香港这块“现金奶牛”,一旦失去,难以替代。对伦敦城里的银行来说,这里就是远东的利润来源,是一条看得见的“金线”。
经济之外,还有政治和战略上的考虑。英国早已不再是一战前的那个“日不落帝国”,但它仍然试图维持一种全球存在感。香港作为英联邦体系在东亚的一个突出点,不仅是金融桥头堡,也是情报与外交活动的重要平台。情报界人士后来回忆,那时候香港在西方情报网络中占有的比重,远远大于它的面积和人口所能说明的一切。
再加上传统的帝国心态作祟。对许多保守党议员来说,旗帜还插在维多利亚港边上,象征意义远大于实际治理的内容。一旦香港完全回归,伦敦政坛很清楚:这不仅是失去一块殖民地的问题,而是在一代人的记忆中,又少了一块帝国残影。对内讲“帝国传统”,对外讲“政治影响力”,香港恰好处于这两者交汇点上。
值得一提的是,英国人并非看不到香港局势的脆弱。新界占全港土地面积九成以上,水源、农地、交通枢纽都在那里。一旦租期届满而新界回归中国,只留下香港岛和九龙这两个“老核心区”,在经济和民生层面几乎站不住脚。这个算术题,在伦敦和香港的英国官员心里都非常清楚。
矛盾恰恰出在这里:英国人舍不得香港,但又担心一旦硬顶,会把多年的经济布局全部砸在自己手里。香港对英国来说,是一块“美味但脆弱”的蛋糕,一动,就可能碎一地。
二、从“打价”到人民大会堂台阶前的一跪
在唐宁街的办公室里,撒切尔夫人先后听取了多位顾问和官员的汇报。中国方面的立场,其实并不隐晦:主权问题不谈判,时间一到,整个香港须回归。这一点,早在1950年代中国新政府宣布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之时,就已经定下基调。
撒切尔是老练的政客,不是对结局全无预见的人。她知道完全维持现状不现实,可她也不愿一上来就接受“全部归还”的方案。在她看来,谈判要先把价码抬到,然后再一点一点往下调,她选择了一套看似有理、实则难以操作的方案。
她的起点是“条约有”的法理逻辑。在英国政府的内部文件里,香港岛和九龙被视作“永久割让”,而新界则是到1997年6月30日为止的租借地。按照这一套思路,撒切尔同意新界在97年归还中国,但坚持认为香港岛和九龙仍应属于英国主权之下。
了解香港地理与经济结构的人都明白,这种切割几乎是不可行的。没有新界提供的水源、农地以及交通通道,孤零零的香港岛和九龙很难维持正常运转。可在伦敦,撒切尔依然把这套说法当成谈判筹码,希望借“法理”说辞拖住局面。
在她的回忆录中,她承认自己曾在内阁会议上提出过出兵香港的想法,理由也是“根据国际法,英国对部分地区拥有主权”。这一设想很快被身边多人认为过于冒险。从军事角度看,英国海军刚刚在南大西洋打一场有限规模的战争就已经精疲力竭;要在80年代与一个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在东亚沿海摊,几乎不存在实际可能。
更具代表的是她各式各样的“折中方案”。共治、托管、联合国参与等等,都是她在不同场合对幕僚提过的点子。她甚至想到“国际托管”模式,希望通过一个多边旗号保住英国在香港的存在。可连她身边的业官员都承认,这些方案逻辑混乱,很难得到中方任何形式的认可。
在反复讨论之后,撒切尔提出了后来颇受关注的“主权换治权”构想:承认1997年中国对香港恢复主权,但要求英国在此之后继续掌握香港的行政管理权,保留一套由英方主导的制度和官僚体系。这套方案在她心中,是“保住实权、放掉名义”的折中选择。
她对外交大臣和顾问说得非常直接:“主权可以谈,但英国须保有实际治理香港的权力。”许多英国官员当时就觉得,这种想法脱离了中国政府一贯公开声明,难以操作。撒切尔依旧坚持,希望至少可以在谈判桌上用它来压价。
1982年9月,她带着这套思路飞抵北京。福克兰战争胜利带来的政治资本,让她的姿态显得格外强硬。英国媒体普遍期待,这位被称为“铁娘子”的相会在东方展现她在国内政坛那种咄咄逼人的风格。
在人民大会堂的那场会晤中,房间里的气氛并不轻松。会谈一开始,撒切尔重申了她对三份旧条约有的立场,强调新界租期可以按期结束,但香港岛与九龙的法律地位应当被视作不同。话锋一转,她提出可以通过协商对条约部分内容进行修改,却明确表示不能接受中方单方面宣布条约无。
邓小平的回答为干脆:“主权问题不能谈。这个问题没有回旋余地。”他指出,新中国成立之后,已经宣布废除一切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特权和不平等条约,其中就包括涉及香港的那些协议。他强调,中国不是晚清政府,也不是签署这些旧约的李鸿章,“如果现在还收不回香港,就无法向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交代。”
关于1997年后的安排,邓小平只给出一个底线:届时中国收回的不只是新界,而是包括香港岛和九龙在内的整个香港地区,这一点没有商量余地。倒是在治理模式上,他表示可以在“一国”的前提下设计“两制”,保持香港原有的资本主义制度和生活方式不变,这部分可以详细磋商。
面对这个立场,撒切尔提出了她的“主权换治权”方案,试图说服中方接受一种“中国拥有主权,英国继续管理”的架构。她甚至提醒,如果不让英国在97年后继续治理香港,可能会对香港的稳定造成“灾难影响”。
邓小平的回应,后来被多方回忆为非常有力度的一段话。他说,小的波动难以避免,如果中英合作得好,大的动荡可以防止。他话锋一转,提出警告:如果港英政府在未来若干年内采取对抗举动,或者大规模撤走资金、破坏香港的经济基础,中国可能就不得不考虑提前或用其他方式收回香港。所谓“灾难影响”,如果真的出现,中国方面也会承担并解决。
在会谈的后,他明确表示,谈判还可以继续,但谈议题有边界:可以商量的是香港如何保持稳定繁荣,包括97年前后的过渡安排,而不是“97年后英国是否继续拥有治权”。他甚至预先设定了一个时间框架——两年内如果达不成协议,中国将单方面公布关于香港的方针政策。
那天上午,会谈结束后,撒切尔走出人民大会堂,在台阶处突然失足,一膝着地。旁边的英国驻华大使柯利达赶紧扶住了她。这一幕被现场媒体捕捉到,预应力钢绞线多电视台不断播放。部分西方媒体用了为夸张的标题,把这次意外比作“大英帝国向中国叩头”。
摔倒的具体原因,英方给出了多种解释:有人提到她大腿曾做过手术,有人说是重感冒导致身体不适,也有版本认为只是跟鞋踩空。但不少观察者还是觉得,这场跌倒带有一种象征意味——强硬的表象下,实际谈判收获有限,心理上的挫败感难免。
三、“铁娘子”的转弯与联合声明的诞生
9月10日,也就是与撒切尔会谈后不久,邓小平接见了曾任英国相的德华·希思。这位在中国有一定好感度的英国政界老将,被视作可以向伦敦传递真实信息的渠道。邓小平明确向希思表明:撒切尔提出的“主权换治权”方式,从根本上说行不通,建议他转达中方立场,劝撒切尔尽快调整思路,以免拖到两年后让中国不得不单方面宣布政策。
与此同时,香港局势也出现了不稳定迹象。谈判立场的分歧,很快传导到金融市场。港元汇率出现波动,股市大幅下挫,对外贸与金融业影响明显。中国在香港的外汇收入受到损失,英资在港的力量亦感到压力。有人评论说,那段时间港英政府“威信受损”,并不夸张。
整个1983年夏季,中英三轮会谈,表面上程序进正常,实质上却很僵硬。中国外长姬鹏飞在谈判桌上的态度相当坚定:1997年,中国须对香港恢复行使完整主权,没有法律和政治空间可以退让。撒切尔在她的著作中写道,自己在这个阶段已经意识到,让香港在97年后成为某种意义上的“英方自治实体”的设想,没有实现的可能。
她在内部文件中记录:“我们不得不面对一个局面,即1997年之后,香港和英国之间不再有权力与责任的法律纽带。”这句话背后,是她强烈的挫败感,“我沮丧了”这样的文字,在她一向强硬的笔调中颇为少见。
不过,她并没有选择掀桌子。在撒切尔看来,如果谈判破裂,让中国提前单方面宣布政策,不仅会对香港造成立即冲击,也会在国际上把英国置于被动位置。所以她调整策略,把“避免谈判破裂”作为要目标,对细节展开拉锯。
之后的两年,中英之间围绕“联合联络小组”“过渡安排”“未来制度设计”等议题,进行了二十多轮磋商。撒切尔本人并未事事亲自出面,但关键节点的态度调整,仍然需要她拍板。
在这些谈判中,英方时不时抛出一些试探的提议,比如后中英联合小组进入香港的时间,或者对部分条款措辞进行模糊处理,希望保留解释空间。中国谈判代表团的回复大多很平衡:在不触及主权和终权力归属的前提下,可以细谈;一旦涉及到英方试图在97年后延伸政治影响,态度立刻收紧。
这种往复拉锯,持续了相当长时间。直观一点说,英国人寄望在文本技术上多留一些空间,而中方则强调政治表达须清晰,避免日后人为制造“灰地带”。
手机号码:152220263331984年9月,中英双方就《中英联合声明》文本达成一致。12月,中英两国政府正式签署这份具有法律力的文件。联合声明确认,中国将在1997年7月1日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,并明确写入香港特别行政区将实行的基本制度框架,这为后来的《基本法》制定提供了基础。
有意思的是,在联合声明谈妥之后,撒切尔的心态仍然带着一丝不甘。她在晚年的著作中再次写到香港问题,强调英国对那些长期为港英政府工作的香港人负有“道义上的责任”,认为一定程度的“保护义务”应该延续下去。这种说法,某种程度上反映了她内心处仍把香港看作英国影响力的一部分。
回到那句后来流传较广的话——“哎呦,邓小平真是残酷啊!”这是撒切尔在离开人民大会堂后,对身边的驻华大使柯利达说的。所谓“残酷”,其实是对方立场非常坚定、不留缝隙的另一种表达。对习惯了英国议会式辩论、惯于在灰地带周旋的政客而言,遇到这种底线清晰的谈判对象,确实不好应付。
在之后某次谈到中国时,撒切尔引用了中国的一句俗语“百闻不如一见”,说对中国的印象“远比在伦敦时听到的复杂得多”。这句略显含蓄的评价,也从侧面说明,那次北京之行对她的冲击不小。
四、钢铁交锋背后的人与算计
很多人提到那场谈判,总用“铁娘子”对上“钢铁公司”这种略带戏谑的说法。撒切尔以格强硬、立场保守著称,而邓小平在国内被称为“钢铁公司总经理”,谈起原则问题同样一寸不让,两人坐在一张桌子上,很难出现客气寒暄式的场景。
当时在场的外国观察者注意到一些细节。邓小平在会谈中时不时抽烟、吐痰,痰盂就摆在不远处。他在讲话到关键处,会随手往痰盂里吐一下,这个动作让不少西方人士印象刻。《撒切尔夫人传》的作者乔纳森·艾特肯提到,邓小平一支接一支地抽烟,谈话节奏很快,态度异常坚决,这种风格让撒切尔“找不到插话的空间”。
有观点认为,这些生活习惯,在重要外事活动中未是自然流露,而是一种有意选择出来的“气场营造”。是否如此,很难下对结论,不过有一件事颇能说明邓小平并非不能控制这些细节。
1978年11月,邓小平与新加坡领导人李光耀在北京进行一次正式会谈。李光耀事先了解过邓小平抽烟和吐痰的习惯,特意让工作人员准备好痰盂和烟灰缸,还在墙上安装排烟管道。结果会谈开始后,邓小平全程没有抽烟,也没有吐痰。傅义在《邓小平时代》中记载,这说明他完全可以根据对象和环境调整自己的表现。
从这个角度看,那次在人民大会堂与撒切尔交锋时,他保持原有的生活节奏,不排除带有某种“示强”的意味。对习惯于英国外交礼仪、讲究姿态和细节的撒切尔来说,这样的场面多少有些不适应。
再回头看英国一侧。撒切尔出身中产律师庭,却把自己塑造成“重振帝国自信”的代表人物。从对付英国工会,到处理福克兰战事,她向来以强硬著称。可在香港问题上,她遇到的对手和议题,与之前面对的英国国内势力完全不同。
中国方面坚持的是国主权和民族尊严,把这个问题提升到“历史欠账一定要了结”的度。对邓小平这一代经历过抗战和新中国成立的人而言,香港问题不仅是现实利益,更与晚清积弱和列强侵略的记忆紧紧绑在一起。条约的签署和废除,不再只是法律文本,而是政治姿态。
撒切尔强调条约有,试图从法律传统和国际习惯出发构建谈判依据;中方则强调新中国成立后统一废除不平等条约的政治决断,把这个问题看作国意志的体现。两种逻辑体系交锋,很难找到折中的“术语空间”。
蒋介石在抗战时期的日记里曾锐评价英国的帝国心态,形容其“自私”“狭隘”,对中国崛起怀有顾虑。时间移到1980年代,英国不再具有当年那样的硬实力,但某些观念惯仍在。撒切尔在公开讲话中,经常用“稳定”“繁荣”“法治”等词汇来形容英国在香港的统治,把自身定位为“文明与秩序”的维护者,这在英国保守派听来顺耳,在北京的听众听上去却难免刺耳。
更微妙的一点在于,撒切尔从头到尾都倾向于把自己塑造成“为香港前途负责的角”。她强调英国的离开不能制造“真空”,强调英方治理经验有助于香港未来。这套话,背后当然有她真心认为自己做的是“负责任选择”的部分,但其中隐藏的优越感和话语位置,也非常明显。
从结果看,中英谈判之所以能够达成联合声明,很大程度上是双方都认识到:在主权归属不容动摇的前提下,尽可能通过程序清晰、文本完备的方式,安排好过渡,才是减少损失、维护香港功能的现实路径。对英国而言,这是一次不得不接受现实的过程;对中国而言,则是一次在原则与灵活之间寻找平衡的过程。
撒切尔晚年回忆当年的谈判,仍难掩不甘。她对香港失去的感慨,夹杂着个人政治生涯的自我评价,也带着老帝国面对历史变迁时的一丝失落。邓小平当年的立场则保持了非常一贯的逻辑:旧账总要结清,时间到了,该回来的终究要回来。
香港问题的解决过程,把这些复杂的情绪、各方的算计以及历史遗留问题,压缩在短短两三年时间里吉安预应力钢绞线价格,变成了一连串会议记录和一份联合声明文本。表面看,只是外交史上的一段谈判史;往里看,却是一段帝国退场与新兴力量上位的缩影。